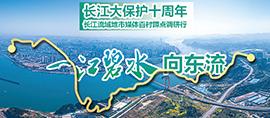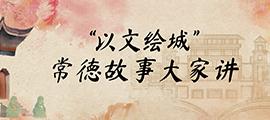■王丕立
四十多年后,我在居住的城市湿地公园看到了儿时的稀罕物——毛蜡烛,一时让我惊诧莫名,那份激动的情绪无法言表。
沿穿紫河两岸散步,一向我只关注两旁堤岸上的花树,前两天我才突然发现,水边的芦苇丛中,一根根枣红的蜡烛状穗子正朝天擎举,用手机里的“辨物识花”软件一拍,果真是曾经的熟识之物,只是没想到它是这样生长在水里的。
毛蜡烛的学名叫香蒲,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生于湖泊、河边、水稻田及湿地,秋季采收果穗,为消炎利尿和止血的良药。
儿时,我们上山砍柴,去田塍打猪草,上缓坡割牛草,脸上、手上、腿上裸露在外的皮肤,总是神不知鬼不觉被划开一道道口子,那是刺苋、芭茅们的杰作,它们挨上我们稚嫩的皮肤,就会豁拉开一道冒着细密血珠的划痕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们会在木板壁上揭下一个个蜘蛛窝,拓在伤口上止血。我们寻找的目标一般是腿细长肚子小的蜘蛛,那些腿短肚子大的蜘蛛,我们避之唯恐不及,它们不仅样貌骇人,还可能藏有毒性,弄不好会让我们感染上蜘蛛毒。
一个露重的夏天早晨,我攀爬到卧室的衣柜顶端,准备撕下靠近房椽的最后一个蜘蛛窝,贴到我右手新划开的伤口上。母亲不知何时站到了卧室门槛外,喊我赶快下来。她扬了扬手中一根玫红色毛蜡烛,说:“这毛蜡烛比蜘蛛窝管用多了。”
我迅速跳到地上,母亲捏起拇指和食指,在烛体上扯下一片絮状的丝绒物,粘到我的伤口上,很快便止了血,刚才还火辣火烧的伤口这会儿便凉飕飕的,一点儿也不疼了。母亲听到我的絮说,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,一扫之前的焦灼和不安。她将毛蜡烛插到板壁上,我感觉家里年长日久烟熏火燎变得漆黑的板壁霎时有了光亮,仿佛有一柱光照拂在房间四周,映得我内心亮堂堂。
多年之后,我去了城里读书、工作,许多次往返城乡之间,再没见到毛蜡烛的踪迹。一次老家生活的姐姐来城里,对我说,家乡的枇杷、桃子、李子没有人采摘享用,她邀请村里人去采摘。那些家庭的老人说,他们的后人现在连城里买来的苹果、香蕉都吃腻了,对乡里的那些水果更不感兴趣。姐姐说完,眼中满是怅惘。
我即刻想到了毛蜡烛,它与那些本土水果一样,在村民心目中也归属于同一类,低廉、寻常,因而不被人们看重。但在我心里,它们具有熠熠生辉的宝藏品质,其光亮闪烁在我身后的岁月长河里,永远给人力量。这一路走来,欢乐与悲苦交织,沉淀在它们身上的故事,激励着我、鼓舞着我去迎接新的挑战。